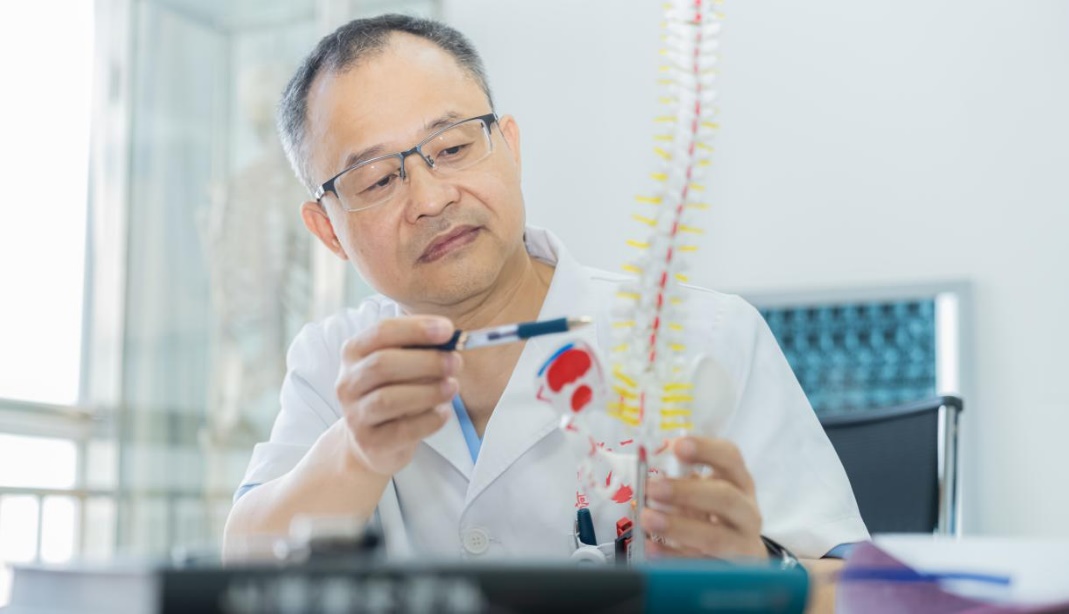蒂莫西·法卡斯(Timothy Farkas)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圣塔内斯山(Santa Ynez)山区捕获并转移了1,500种竹节虫。他的主要工具是木棍。
法卡斯说:“感觉有点野蛮。”“渊博只是从地面上捡起一根棍子,然后从灌木丛中打败了垃圾。”这种低技术手段驱散了成群的棒虫,该团队很容易地将污垢清除了。
在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外的这个山坡上,有两种昆虫(Timema cristinae)栖息于灌木丛中。该生物具有两种相应的颜色:绿色和条纹。法卡斯(Farkas)和他的生态学家们知道,竹节虫已经进化为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但是研究人员想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扭转这种关系,从而使进化的“伪装”特征会影响生物生态。
为了找到答案,研究小组将绿色和条纹昆虫的混合物移到了不同的植物上,使一些昆虫的颜色与新家发生了冲突。这些昆虫突然适应不良,成为饥饿的鸟类的攻击目标,并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1。被不匹配的竹节虫吸引到灌木丛中的鸟被困在周围,以吃掉其他居民,例如毛毛虫和甲虫,使一些植物变得干净。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的生态学家法卡斯说:“这种进化力会导致局部灭绝的现象令人震惊。”“这影响了整个社区。”所有这些都是由于过时的进化特征而发生的。
生态学家在研究其系统时通常会忽略进化。他们认为无法测试如此缓慢的过程是否可以在可观察的时间尺度上改变生态系统。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进化比想象的要快得多,并且一波研究已经利用这一思想来一致地观察进化和生态学。
这样的生态进化动力学对于理解新种群的出现或预测何时灭绝很重要。实验表明,进化变化会改变某些生态系统,就像改变传统生态元素(例如到达栖息地的光量)的变化一样。雅典佐治亚大学的生态学家特洛伊·西蒙(Troy Simon)说:“共同进化的动力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追逐的巨龙”。
快速发展有时可以抵消气候变暖和其他已知变化驱动因素的某些不利影响;在其他情况下,它会使这些影响恶化。研究人员说,即使对于最常见的过程,例如人口规模变化或食物链变化,生态学家也必须考虑进化。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进化生态学家安德鲁·亨德利(Andrew Hendry)说:“每个人都意识到迅速的进化无处不在。”
反向达尔文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查尔斯·达尔文·芬奇。当博物学家于1835年访问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时,他记录了生活在不同岛屿上并食用不同食物的雀科喙的一些变化。在航行的几年后,他在《研究杂志》中暗示,这种变化表明鸟类的生态与其进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
达尔文从未想象过要在行动中看到它,因为他认为进化只在“千古流逝”时发生?但是到1990年代后期,生态学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可以在给定物种的几代人内观察到进化,这是他们可以使用的时间尺度。
能够快速生存和死亡的生物提供了一些早期数据,证明了进化是如何影响生态的。2003年发表的一项关键研究2集中在藻类和轮虫(以藻类为食的微观捕食者)上。这两个物种都可以在几周内完成多达20代的滴答。这项研究将这些生物在水箱中混合在一起,结果表明,当藻类迅速进化时,它们会摆脱正常的“捕食者”灰色种群动态。
通常,这两个物种在“缩放”和“灰尘”之间形成循环。藻类种群不断增长;轮虫然后吞噬它们,它们自己的种群爆炸。当捕食者耗尽藻类时,它们的数量就会崩溃。藻类随后反弹,并且模式再次开始。但是,当研究人员引入不同的藻种(“具有一定的遗传多样性”)后,藻类开始迅速进化,并且循环完全改变。由于新藻类对捕食的抵抗力增强,藻类种群保持较高水平的时间更长,轮虫的繁荣异常延迟。
对蚜虫3和水蚤4的类似研究已经证实,快速进化会影响种群的特征,例如种群的生长速度。这些生态变化可以改变未来的进化和选择。看到行动如此迅速的变化,已经改变了生态学家对他们认为是可预测的基本生态过程的印象,并表明了研究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时考虑进化的重要性。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的生态学家斯蒂芬·埃纳说:“鉴于进化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必须重新审视有关生态的一切。”“他改变了一切。”?/ p>
假湖
在进行了这些最初的实验室研究之后,生态学家开始思考更大的想法。在室内进行的小规模实验可以再现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因此研究人员已经在更大,更少人造的环境中测试了他们的想法。
弗拉格斯塔夫北部亚利桑那大学的进化生态学家丽贝卡·贝斯特(Rebecca Best)说,弄清生态进化动力学是否会影响现实世界是该领域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如此多不可控制的因素会影响野生生态系统。
她通过将自然元素纳入严格控制的实验中找到了中间立场。在一个俯瞰瑞士卢塞恩湖的地方,她和她的团队建立了50个微型湖泊:每个装有1000升水的大型塑料水箱,以及从三个湖泊收集来的泥沙,植物生命,藻类,无脊椎动物和水的浆液。 ,康斯坦斯和卢塞恩。一旦这些“生物壁”定居下来,浮游生物繁殖并植株生根,研究小组便将每个成年的三脊椎棘背stick(Gasterosteus aculeatus)在遗传上不同的谱系之一引入每个池中:一个来自康斯坦茨湖,另一个来自日内瓦湖。 。几周后,研究人员移走了这条鱼,并用两个地方的实验室饲养的幼鱼以及这两个系的一些杂种代替了它们。
他们发现5,成年人如何操纵其环境影响了下一代鱼类的生存(见“鱼腥反馈”)。例如,如果成年鱼去除了一定大小的猎物,则与成年鱼具有共同特征的幼鱼(在这种情况下,嘴巴大小)就饿了。与以前的居住者不同的少年生活得更好。研究表明,成鱼的性状决定了下一代的环境,足以决定其后代的进化轨迹。
Best说她的中观实验比实验室研究更为复杂和现实,但较不容易控制。她说,理想情况下,该团队将在野外进行实验,但这会带来自己的障碍,例如必须考虑生态系统中其他物种的进化,或发生极端风暴等事件的风险。
诸如Best之类的实验“比自然界中的任何事情都容易得多,而且受到更多的控制”?亨德利说。但是它们可能无法反映实际生态系统中发生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处于分水岭。这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了作用吗??/ p>
在混乱的现实世界中,很难确定单个特征的影响,无论是生态属性(例如降雨)还是演化特征(例如伪装的变化)。
无论如何,一些勇敢的生态学家正在尝试。去年,对特立尼达的孔雀鱼的研究6表明,鱼类的进化可以像环境因素一样强烈地推动生态变化:可利用的光量。
该研究集中于该岛北部的两个孔雀鱼种群(Poecilia reticulata)。它们的生境在几个生态特征上有所不同,包括它们从林冠层中获得多少阴影,从而影响溪流中藻类的生长。
该研究小组将小孔雀种群转移到流域的八条河流之间,这些种群的进化特征不同,例如身体比例和颜色,并测量了冠层。在一些研究地点,引入一种新型的孔雀鱼改变了藻类种群,从而使更多的20%的光流到了水中。研究人员说,即使是自然生态系统,也是进化和生态的产物。
这个实验确实比其他许多实验都使用了更自然的环境,但是特立尼达孔雀鱼是在数百项研究中都出现过的生态名人,他们所居住的河流已经受到了高度控制。麦吉尔的生态学家格雷戈尔·福斯曼(Gregor Fussmann)说,研究人员想知道在孔雀鱼种群中起作用的力量是否也在不一定以进化动力学着称的物种中发挥作用。他说:“需要通用的系统。”
蜥蜴四肢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进化生态学家托马斯·斯科纳(Thomas Schoener)和他的团队正是要对巴哈马的两只蜥蜴进行研究。他们的项目是一项始于1977年的正在进行的多代研究的一部分。他们一直在尝试通过捕捉卷尾蜥蜴(Leiocephalus carinatus)并将它们移至一串由棕Anoles(Anolis sagrei)居住的小岛上来模拟加速进化,从而观察生态系统的变化。
弯尾是较小的棕色Anole的天然天敌,因此,当团队首次将弯尾移到带有Anoles的岛屿上时,后者的种群减少了。蜘蛛种群中的主要捕食者“ Anoles”受到袭击时,蜘蛛种群增加了,多余的蜘蛛又吃了更多的跳虫(Collembola)。研究人员发现幸存的逃逸者逃到树上逃脱了新的捕食者,从而引发了对植物的破坏。该团队从以前的工作中知道8,通过选择后肢较短的后代,Anole很快适应了攀树。
但是随后发生了意外情况。2011年,艾琳飓风袭击了这些岛屿,随后在2012年袭击了桑迪飓风。蜥蜴和卷尾蜥蜴的数量都崩溃了。在某些岛屿上,暴风雨过后,肛门被完全消灭了。
斯科纳说:“飓风是好运,因为一方面,飓风给了我们有关干扰的各种有趣数据。”“另一方面,它可以减缓正常的进化进程。” / p>
该团队设法保持其项目进度,并观察了飓风过后腿长和蜥蜴的重新殖民化的进化变化。
出乎意料的是,在飓风中幸存下来的肛门比飓风前种群更长的肢体7 –与团队预测相反,但是对于在暴风雨中紧紧抓住树枝可能更好。该团队刚刚获得资金,用于研究这种进化变化将如何影响生态系统。
飓风无疑使Schoener的研究复杂化,但是其他研究人员赞赏这种计划外的干预措施,因为它为研究真实事件的后果以及观看蜥蜴重新定居岛屿提供了机会。最好的说,即使在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任何数量的动力学也可能改变生物体进化的过程。“其潜在的相互作用正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发生。” / p>
她和其他人说,在实验室和更详尽的实地研究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些研究人员希望将遗传数据添加到他们的工作中,以首先了解是什么在推动进化。这将告诉他们特定的性状(例如“生长率”)是否真正可遗传和进化,而不是可以直接受到动物环境影响的特征。基因组数据还可以帮助发现可能影响生态的“比体型或生长速度更难观察”的隐藏特征。
在一项关于藻类和轮虫的研究9中,德国比尔森马克斯·普朗克进化生物学研究所的进化生态学家卢茨·贝克斯和他的同事们观察了几个周期,随着藻类聚集在一起并散布,种群不断增加和减少。但是,当研究小组研究团聚行为背后的个体基因时,他们发现即使一个团簇看起来都一样,它们的表达在一个周期到另一个周期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从那以后,他们观察到三种物种“藻类,轮虫和病毒”共同进化,发现轮虫减慢了藻类和病毒共同进化的速度。研究小组计划重复这种类型的实验,分析基因组数据,以观察藻类和病毒基因的具体细节如何随时间变化。贝克斯说:“我想到达一个可以实际预测快速进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基因组架构的地步。”
快速发展可以“至少部分地”抵消气候变化和其他生态干扰的破坏作用。例如,2011年,由埃勒纳(Ellner)领导的一个小组重新分析了35年来从康斯坦茨湖沉积岩心中挖出的蚤水蚤卵中35年的数据。数据表示湖水受到蓝细菌水华影响的时间之前,期间和之后,该细菌对水蚤的营养价值较低。研究小组发现,随着水蚤食物的营养降低,少年跳蚤的生长变差,最终成年后成年。但是经过几代人的进化变化,导致少年的增长率恢复到正常水平。尽管它们没有达到开花前的大小,但成年人恢复了一些失去的身材。研究人员认为,当环境变化时,快速进化最有可能发生,但由于它们的方向相反,其影响被隐藏了。厄尔纳说:“进化将成为生物圈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
当法卡斯(Farkas)击败圣芭芭拉(Santa Barbara)周围的灌木丛并整理竹节虫时,他脑海中浮现出这些有关进化和生态的问题。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计划更加精心的计划。他们希望在收集遗传数据的同时捕捉到一个完整的反馈周期,即“影响生态的进化再次影响生态”。Farkas说:“对进化的这些影响有多大,以及了解何时何地发生进化将变得很重要。”我,这是最后的疆界。但这要花很长时间。
自然554,19-21(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