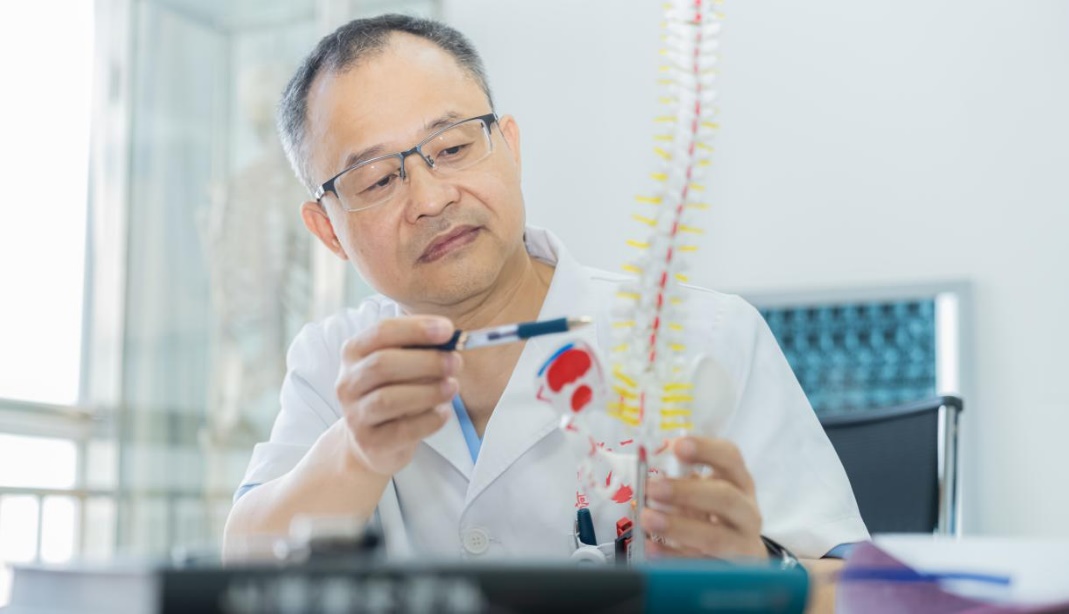遗传学家罗特姆·索雷克(Rotem Sorek)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他的细菌病了,如此之好。他故意用一种病毒感染了它们,以测试每个生病的微生物是独自作战还是与盟友交流以抵抗攻击。
但是当他和他位于以色列雷霍沃特的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小组检查烧瓶中的东西时,却发现完全出乎意料的东西:细菌沉默了,病毒viruses绕了,向每个容器传递了音符其他只有分子能理解的语言。他们正在共同决定何时躺在宿主细胞中的低处,何时复制并爆发,以寻找新的受害者。
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将从根本上改变科学家对病毒行为的理解。
感染细菌的病毒,即称为噬菌体(或噬菌体)的尖棒棒糖状生物,具有监视机制,可根据是否有新鲜的受害者,使它们了解是否保持休眠或攻击。但是研究人员长期以来认为这些过程是被动的。噬菌体似乎只是坐下来聆听,等待细菌窘迫信号到达发烧音,然后采取行动。
索雷克和他的同事发现噬菌体正在积极讨论他们的选择。他们意识到,当噬菌体感染细胞时,它会释放一种微小的蛋白质-一种只有六个氨基酸长的肽-可以向其弟兄传达信息:“泪”受害了吗?随着噬菌体感染更多的细胞,消息变得更大,表明未感染的宿主正在变得稀缺。然后噬菌体阻止了裂解(即复制和脱离宿主的过程),而不是隐藏在被称为溶原性的缓慢状态中。
事实证明,这些病毒并不依赖细菌线索来做出决定。他们控制自己的命运。“他的发现是病毒学领域一个重要的,重要的,革命性的概念,”中国成都大学的结构微生物学家韦成说。
Sorek将该病毒肽命名为“ bibitrium”。拉丁词后再作决定。它似乎很像细菌“群体感应”所使用的通信系统,以共享有关细胞密度的信息并相应地调整种群。但是,这是任何人第一次在病毒中展示这种分子信息。而且,与科学家所称赞的一样,更复杂的社会媒介也融入了病毒的新形象。
病毒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孤立地研究他们的受试者,只针对具有单个病毒颗粒的细胞。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许多病毒可以合作,共同感染宿主并破坏抗病毒免疫防御能力。
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可能一直在进行错误的实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萨姆·戴兹-穆卡兹说:“这已经撼动了病毒学的基础之一。”
学习这些病毒相互作用背后的语言可以为癌症和讨厌的超级感染的新治疗方法的设计提供信息。病毒的社会偏爱甚至有助于解释它们如何逃避称为CRISPR的细菌免疫系统。“从表面上看,它真的很强大,” Deraz-Mu帽oz说。
社会研究
科学家在1940年代首次发现了混合病毒,当时生物物理学家Max DelbrBrck和细菌学家Alfred Hershey分别进行的实验表明,两个病毒颗粒可以同时侵入同一细胞并交换基因。但是,据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分子遗传学家,德尔布吕克大学的茅特茅说,戴尔·凯泽(Dale Kaiser)说,这些早期观察结果只是对科学家们来说才是真正有趣的实验方法,它们使研究人员能够在两种病毒之间建立杂交株。错过了与基本生物学的相关性。
直到1999年,才有人注意到这种病毒本身取得了什么合作。那年,现任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保罗·特纳和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林超证明,噬菌体在囚犯困境战略游戏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并以自己的利益为己任2。
随后的其他有益病毒相互作用的例子包括与引起诸如肝炎,脊髓灰质炎,麻疹和流感等疾病的病原体有关的相互作用。它们通常发生在不同的病毒株之间,这些病毒株在提高自身繁殖机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这些合作特征的分子基础-“交流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难以捉摸。正如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的进化遗传学家Rafael Sanju谩n指出的那样:“这里的“流动”真的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发现Arbitrium在该领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在Sorek首次描述这一现象之后,几乎在2017年,四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包括Cheng和一个由西班牙巴伦西亚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结构生物学家Alberto Marina领导的研究小组)着手试图揭示Arbitrium肽的分子基础。由噬菌体产生,感知和作用。
这些技术细节在过去的9个月中发表在5篇论文中,7有助于准确解释Sorek发现的短肽如何影响病毒的决策。但是,对于Marina来说,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他怀疑通信系统可能会提供更多功能。
玛丽娜的怀疑取决于其中一篇论文的发现6。Marina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微生物学家Jos茅Penad茅s的合作表明,噬菌体中的Arbitrium受体不仅可以与细菌中有助于病毒繁殖的基因相互作用,而且还可以与其他不相关的基因相互作用DNA片段。这意味着其活动可能不仅仅限于病毒的“走走停停”决定。研究人员现在正在研究噬菌体肽语言是否也改变了受害者体内关键基因的活性。“真的,”玛丽娜说,“他会让照片变得更大,更令人兴奋。”?/ p>
扩展自己的最初发现,Sorek发现到处都出现了Arbitrium肽。他的团队现在已经发现了至少15种不同类型的噬菌体,所有这些噬菌体都可以感染土壤微生物并使用某种短肽进行交流8。索雷克说,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噬菌体似乎用不同的语言说话,只能听懂自己的语言”?因此,病毒聊天可以发展为只允许近亲之间的交流。
噬菌体可能只讲自己的种类,但也可以听其他语言。分子生物学家邦妮·巴斯勒(Bonnie Bassler)和她的研究生贾斯汀·西尔普(Justin Silpe)发现,病毒可以利用细菌释放的群体感应化学物质来确定何时开始繁殖和谋杀的最佳时机9。“噬菌体正在监听,它们是出于自己的目的劫持主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是为了杀死主机。” Bassler解释说。
这种分子监听在感染霍乱霍乱弧菌的噬菌体中自然发生。但是,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中,Bassler和Silpe设计了“荣荣”噬菌体,它们可以感应其他微生物(包括大肠杆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特有的信号并消除它们。实际上,这些病毒变成了可编程的刺客,可以随意杀灭所有细菌。
为了更大的利益
某些病毒式的合作似乎在利他主义的边缘。去年有两个独立的小组报告说,一些噬菌体会无私地采取行动来克服假单胞菌细菌的病毒对策10,11。
观察小组观察到病毒感染了专门针对微生物的细菌,这些研究小组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噬菌体生物学家乔·邦迪-德诺姆领导,而CRISPR专家Edze Westra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病毒学家Stineke van Houte领导。旨在破坏细胞基于CRISPR的免疫防御的蛋白质。第一波病毒攻击细胞,杀死自己但也削弱了细菌。最初的轰炸为其他人征服微生物的敌人铺平了道路。Bondy-Denomy说:“在另一个噬菌体出现并成功之前,它们的噬菌体必须在那里存在并死亡,并产生抗CRISPRs。”
在后续工作中,韦斯特拉(Westra)和他的博士后安妮·奇瓦勒罗(Anne Chevallereau)证明了缺乏这些抗CRISPR蛋白的噬菌体如何能够利用其他抗CRISPR蛋白的合作产品。对于韦斯特拉(Westra),这表明病毒之间无私行为的潜在深远影响。他说:“在人口层面上有很多新兴属性。”“牢记这些噬菌体的生态非常重要。” / p>
德克萨斯大学农工大学噬菌体技术中心的生物物理学家曾兰英说,这些噬菌体之间交流与合作的例子可能只是社会矛头。“这是整个未开发的区域。”感染其他细胞类型的病毒(包括动物和人类细胞)也是如此,它们利用了自己的一些社交技巧。
以水疱性口炎病毒(VSV)为例,该病毒主要感染农场动物,但也会在人类中引起流感样疾病。正如Sanju谩n和他的同事所显示的那样,这种病毒病原体的颗粒以个人代价抑制了宿主的免疫力,但对他们却有利。还没有人知道这种合作回避是如何发生的,但是这项工作凸显了利他主义对于VSV的成功至关重要。这可以帮助科学家在农场动物中击败该病毒,并对其进行优化以用于疫苗和治疗药物。
集体行动的其他实例在引起疾病的病毒中也很普遍。例如,在脊髓灰质炎病毒中,多种遗传上不同的病毒株可以聚集在一起,以交换基因产物并增强其杀灭人类细胞的潜力14。当将两种流感病毒一起培养时,与分开放置相比,它们的生长更好。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在流感患者的鼻拭子中,这两种病毒株似乎并存。领导该研究的华盛顿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杰西·布鲁姆(Jesse Bloom)认为,这与流感病毒的某些特性有关,即“生命”,其种群规模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合作性颗粒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黏在一起。对于不经历此类传播瓶颈的病毒,“在现实环境中可能更可能维护操作系统”?他说。
显微镜学家Nihal Altan-Bonnet研究轮状病毒在小鼠幼崽之间的传播时发现的正是这一点。轮状病毒颗粒可以在气泡状小泡中的细胞之间一起传播,共享资源并躲避宿主免疫系统。而且,Altan-Bonnet和她的同事们已经表明,当这些颗粒位于这些合作簇中时,它们比单独传播时对小鼠更具感染力17。
现在还知道许多其他病原病毒,包括引起寨卡病毒,肝炎,水痘,诺如病毒和普通感冒的病毒,也可以通过这些囊泡传播。
“这些病毒非常狡猾,”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心脏,肺和血液研究所的宿主病原体动力学实验室负责人Altan-Bonnet说。“我们必须考虑破坏这种协作性和病毒群集的策略。”?/ p>
也就是说,除非可以充分利用病毒的破坏力。数个小组正在测试噬菌体作为细菌感染的治疗方法,并且更多地了解它们如何相互交谈可以帮助改进此类疗法,这些疗法在医学上已有悠久的历史,但才刚刚开始为获得治疗收益而被操纵。
参与噬菌体
例如,上个月,研究人员描述了基因工程噬菌体首次成功用于临床治疗耐药细菌感染的方法18。当然,对于这种感染,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病毒彻底消灭细菌。但是对于以微生物失衡为特征的疾病,例如痤疮,某些类型的癌症和炎症性肠病,最好部署可以帮助恢复平衡而无需全力进攻的噬菌体。
对于那些更微妙的应用程序,确切地知道病毒是如何通信的“对帮助我们设计可用于治疗疾病的噬菌体真的很有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噬菌体生物学家Karen Maxwell说。因此,进入Arbitrium系统可能会导致更易处理甚至可逆的治疗。
学习说病毒也可以提供另一种治疗益处。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的微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奥特里(Christopher Alteri)说:“他可能是合成生物学工具包的补充,可以帮助微调工程细菌基因的表达。”
举例来说,Sorek已将Arbitrium肽从其在噬菌体中的自然栖息地中带出,然后将其插入其他生物中,在它们中充当调光开关,从而调高或抑制基因活性。在未发表的论文中,他和他的研究生佐哈尔·埃雷兹(Zohar Erez)将双歧机械插入了枯草芽孢杆菌细菌中,使他们可以随意操纵其几个基因。经过改造的微生物有一天可以用于例如以精确剂量或将药物递送到特定位置。
Sorek指出,如果在人类病毒中保留类似类Arbitrium的系统,那么“病原体,例如HIV和单纯疱疹病毒,像噬菌体一样,将其一生中的一部分藏匿在细胞中”,那么任何通讯分子提示病毒休眠“立即变成药物”?
每个坚持不懈的科学项目都将获得“学”。社交病毒的研究也不例外。两年前,Sanju谩n的Drickaz-Mu帽oz和英国牛津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Stu West创造了一个新术语“社会病毒学”,以为其研究提供框架。美国微生物学会将在本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主办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针对该主题的研讨会。“是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 Deraz-Mu帽oz说。
在社会病毒学中,他看到了与过去几年逐渐被细菌中相似的群体行为所接受的许多相似之处:直到研究人员查明了群体感应中涉及的化学物质并为该过程命名后,大多数微生物学家才对此现象给予了任何关注。
迪兹·阿兹·穆帽兹说:“意识中没有”。但是,与所有社交和病毒式传播一样,信息也在传播。
自然570,290-292(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