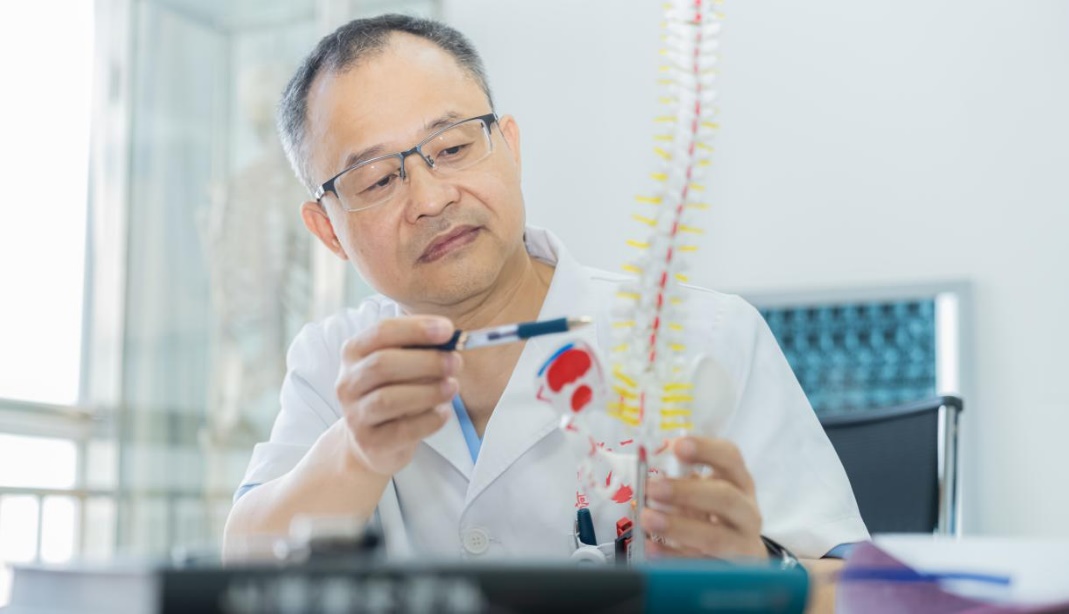这张图片显示了保存的,重建的遗骸,被称为Sasha的婴儿羊毛犀牛的遗骸。
由于气候变化,羊毛犀牛可能会灭绝,没有过度彻底。
史前百万南的灭绝在最后一次冰河时代末端的羊毛猛犸象,洞穴和羊毛犀牛,往往归因于全球早期人类的传播。虽然过度迟到导致一些物种的消亡,但今天(8月13日)的研究中出现在当前生物学中的研究中,羊毛犀牛的灭绝可能具有不同的原因:气候变化。通过从这一群这些巨型的巨型疣测定古代DNA,研究人员发现,羊毛犀牛种群仍然稳定并且持续存在,直到它从西伯利亚消失之前只有几千年,当温度可能对冷适应的物种过高时。
“最初认为人类出现在西伯利亚东北十四或五十年前,当时羊毛犀牛灭绝了。然而,最近,有几个较老的人类占用场所的发现,最着名的是大约三万岁,“古代生物中心的进化遗传学教授,父母的高级作者LoveDalén(@Love_Dalen)说斯德哥尔摩大学之间的合资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以,对羊毛犀牛的灭绝的下降与该地区人类的第一次出现不一致。如果有的话,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一些看起来有点像在此期间人口大小的增加。“

此图像显示羊毛犀牛骨架。
为了了解西伯利亚羊毛犀牛种群的大小和稳定性,研究人员研究了来自组织,骨骼和14次杀虫样品的DNA。“我们测序了一个完整的核基因组以回顾时间并估计人口尺寸,我们还测量了十四个线粒体基因组,以估计女性有效的人口尺寸,”博士生(@Edanalord),一名博士学位古代遗传学中心。
通过观察这些基因组的杂合子或遗传恒定,研究人员能够在灭绝前几千年来估计羊毛犀牛人口。“我们研究了人口大小和估计繁殖的人口规模和估计的变化,”Paleogenetics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Co-First Autory Nicolas Dussex说。“我们发现,在大约29,000年前寒冷时期的人口大小增加后,羊毛犀牛人口大小仍然是恒定的,此时,近亲繁殖很低。”

这张图片显示了埃德纳勋爵在实验室中抽样了羊毛犀牛DNA。
这种稳定性持续到人类在西伯利亚开始良好,对比将预期的下降,如果羊毛犀牛因狩猎而灭绝。“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主说。“我们实际上在29,000年前,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人口大小减少。我们看起来只有18,500年前的数据,这是濒临灭绝的约4500年,所以它意味着他们在那间差距中拒绝了。“
DNA数据还揭示了遗传突变,帮助羊毛犀牛适应较冷的天气。这些突变中的一种,皮肤中的一种受体,用于感测温暖和寒冷的温度,也存在于羊毛般的猛犸象中。这样的适应表明,由于简短的温暖时期的热量,被称为Bølling-Allerød壁垒的热量,羊毛犀牛,这些犀牛尤其适用于西伯利亚气候,这可能已经下降,这是恰好濒临灭绝最后的冰河时代。
“一旦进入一个环境,我们就远离人类的想法即将夺走一切,而是阐明了气候在梅格法纳尔灭绝中的作用,”主啊。“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人类参与,但我们建议羊毛犀牛的灭绝更可能与气候有关。”
研究人员希望研究额外的羊毛钻的DNA,这些猪笼饲料中居住在他们测序的最后一个基因组之间的至关重要的4,500年间隙和灭绝。“我们现在想要做的就是尝试从犀牛那里获得更多的基因组序列,这是十八到十四千年之间的,因为在某些时候,他们肯定必须下降,”Dalén说。研究人员也在看其他冷适应的Megafauna,看看变暖,不稳定的气候有什么进一步影响。“我们知道气候变化了很多,但问题是:不同的动物受到了多少影响,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
参考:“羊毛犀牛的预灭绝人口稳定性和基因组特征”由Edana Lord,Nicolas Dussex,Marcin Kierczak,DavidDíz-del-Molino,Oliver A. Ryder,David Wg Stanton,M. Thomas P.Gilbert,Fátima Sánchez-Barreiro,Guojie Zhang,Mikkel-Holger S. Sinding,Eline D. Lorenzen,Eske Willerev,Albert Protopov,Fedor Shidlovskiy,Sergey Fedorov,HervéBocherens,Senthilvel KSSNathan,Benoit Goossens,Johannes Van der Plicht,Yvonne L. Chan,Stefan Prost,Olga Potapova,Irina Kirillova,Adrian M. Lister,彼得D. Heintzman,Joshua D.Kapp,Beth Shaplo,Sergey Vartanyan,AndersGötherström和爱情达尔,8月13日,目前的生物学.DOI:
10.1016 / J.CUB.2020.07.046
这项工作得到了Formas,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Carl Trygers基金会,欧洲研究委员会合并者奖,以及Knut和Alice Wallenberg基金会。